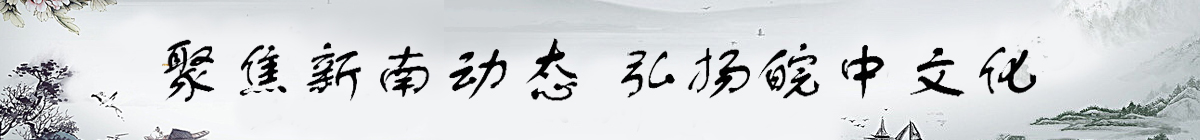少年朱践耳,在病榻上写过一首艺术歌曲《孤独》;五十多年后,他自言“才悟到‘孤独’一词的哲学真谛”。和肖斯塔科维奇一样,他把名字的音调化作“签名”旋律,嵌入《第八交响曲》,只用一把大提琴、一套敲击乐的“二人乐队”,写就一曲“内心独白”——“探索者的心是孤独的”(题记)。
这是他最满意的作品,标题“求索”,写的正是他的一生——自改名“践耳”(实践聂耳)始,于“革命梦”与“交响梦”之间,曲折求索的一生。
拯救
他安卧在棺中,脸上带着微笑。过去他很少放声大笑,而仅仅是会心一笑,有时即使被尖锐质问也默不做声。友人回忆其弥留之际,“除了不知为何总是合不拢的嘴,他的脸仍是那样地平静、温和,一如他生前惯有的慈祥、亲切模样。”
他很早便立下遗嘱:遗体捐献医学研究,家中不设灵堂、不召开追悼会以及任何形式的追思纪念会。就连相伴60年的一架老钢琴,也在不久前捐献给了正在筹备中的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。官方讣告发布,但噩耗的波澜似乎未能越过音乐界和沪京两地——
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、著名作曲家、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获得者、上海交响乐团驻团作曲家朱践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,于2017年8月15日上午9时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,享年95岁。
以63岁“高龄”开启“衰年变法”后,他几乎一年一部交响曲,每一部都力求“解决一个问题,作一新的探索”;他曾获瑞士“玛丽·何赛皇后”国际作曲比赛大奖,名列业界权威的《新格罗夫音乐大辞典》,被音乐界奉为中国交响乐“巨匠”和“丰碑”。但是,在多数大众媒体的讣闻上,他名字前的定语是“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曲作者”。
1986 年,朱践耳《第一交响曲》在北京音乐厅首演。座谈会上,音乐家叶小纲罗列了他在“文革”前几年创作的诸多歌曲。九年后在厦门召开的京沪闽作曲家研讨会上,以大量少数民族音乐磁带录音为材料的《第六交响曲》引发争议。音乐家赵晓生当面提出,《第六交响曲》革新步伐太快,技巧、手段似乎盖过情感本身,“和当年的名作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体现作曲家的真诚、催人向前奋进的力量,反差很大。”
甚至连德高望重的指挥家李德伦,同年在海外接受采访时也说,“‘文革’时他很‘乖’,‘四人帮’一粉碎,他马上就反,他是太赶时髦了……后来就玩现代派了,现代得不得了,作曲变成数学练习,作曲手法玩得很花,已经不再表现人的感情。”
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朱践耳?上述许多音乐界人士都有过同样的疑问。朱践耳在两次讨论现场并未作声,只在私下对友人说,这个问题令他也很痛苦,但那些情感在当时都是真实的。他最终未将那些早期名作列入个人作品集,它们的署名是“践耳”。
遗体告别式上,没有奏响他的交响乐章,虽然龙华烈士纪念馆里曾不断循环播放他的弦乐作品《怀念》;有普通爱乐者抱着大幅合影前来,也有领导现身不久匆匆告退。白纸黑字的主题词仓促覆盖红色LED屏,依稀还透着字样笔画的红光。仪式临近尾声,纸片掉落,忽地露出一个“惠”字,仿佛是他对在场同样年逾九十的爱妻舒群的告慰。
不过,在中国作曲家中,他所沐浴的荣光已然罕有。当许多人的作品难逃“压箱底”的命运,1975年起成为上海交响乐团驻团作曲家的朱践耳,绝大多数作品都已由著名指挥家陈燮阳执棒指挥乐团首演,并录制了多张唱片;近15年来,他先后出版了多部个人交响曲集、管弦乐曲集、作品集,还有2015年底问世的大部头《朱践耳创作回忆录》;作为“上海老艺术家作品数字化抢救工程”的首位受益人,他收藏的各类载体的个人作品,化为30盘光碟,共计1869分钟,目录就多达50页。
2016年10月17日,朱践耳作品专场音乐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。94岁的朱践耳在音乐会结束后执意上台,赠上亲笔题写的一幅字——“深切感谢上海交响乐团拯救了我的‘交响梦’。”夫人舒群后来说,这是他一夜辗转反侧、绞尽脑汁才想出的最贴切的两个字,“拯救!”

2016年10月17日,朱践耳作品专场音乐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(受访者提供)
三级跳
“贝多芬(1770-1827)艺术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持续不断的演化和步幅巨大的迈进……在多年的时间过程中从不停息,由此形成早、中、晚三个明晰的风格单位……这一过程堪称人生体验和艺术风格双重意义上的‘三级跳’,其中大有深意。
“贝多芬的艺术风格成长与其人生的磨难和历练又构成惊人的同步……对于贝多芬,音乐既是生活的回应,也是人生的探索;创作既是生命体验的记录,也是生命体悟的通道:如贝多芬自己所言,‘来自心灵———但愿———回到心灵’。”
8月8日,《文汇报·笔会》刊登了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的文章《贝多芬的“三级跳”》。当晚,朱践耳端着报纸,在字里行间密密匝匝地做出勾画,并在标题右下方写下“保留此文”四字小楷。次日凌晨,他突发中风,再没有苏醒过来。“这可能是他神志清醒时的最后字迹了!”在病房里,舒群拿出报纸,缓缓对杨燕迪说。
早在2002年,作曲家王西麟就曾用“三级跳”归纳朱践耳的创作生涯:“从新四军跳到莫斯科,从莫斯科跳到先锋派”,“这三个历史阶段的过程是十分艰辛,十分深刻,又十分巨大的艺术超越。”对于此说,朱践耳颇感生动、确切,仅做了一点补充说明:“在参加新四军之前,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‘交响乐迷’五年哩!”加上它,就成“四级跳”了。
那并不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。当时他还叫朱荣实,字朴臣,祖辈为第一代民族工商业家。从小家道中落,父母先后病逝,排行老四的他,性格内向、木讷和自卑,音乐是他内心保留的一块小天地。奈何1940年初投考上海国立音专作曲专业未成,不久慢性支气管扩张的老毛病又发作,吐血不止,险些丧命。
在上海,这片中国交响乐的发源地,朱践耳卧病在床两年半,犹如身处“孤岛”中的“孤岛”。幸有一台借来的收音机排忧解闷:肖斯塔科维奇最新的《第五交响曲》、斯特拉文斯基的三部代表作,还有德彪西、拉威尔、普契尼……尤为共鸣的是贝多芬的《第五交响曲》。在他耳中,那不只是“命运之神在敲门”,更是“贝多芬心目中的命运”,时而是恐怖的威胁,时而是对命运的鄙视,时而又是对命运的抗争。
受师长和亲友影响,也受苏联革命歌曲熏陶,朱践耳对红色解放区和自由民主理想充满向往。他在病中改名“践耳”,顾名思义:一是追随聂耳“走革命音乐之路”;二是实践其未完成的志愿,“去苏联留学,写交响乐。”虽然“不自量力”,他还是要说,自己的理想就是“聂耳加贝多芬”。
1945年8月,大病初愈的他,追上妹妹的步伐,投奔苏北抗日根据地,一张五线谱纸都没带。“只有革命胜利之后才谈得上音乐艺术!说不定我已看不到那天了。”这是朱践耳第一次毅然放下“交响梦”,一心要去实现“革命梦”,他为原创歌曲《梦》填词:“一个火红绚烂的梦,我梦见,我有金的翼,振起翼,振起翼,在蓝天白云间。”
乐评人杨宁称,早期朱践耳的艺术歌曲“哀而不伤,只靠旋律与和声的婉转含蓄地表达情感”,即便在这首写于病情好转、表达渴望投身“红色的梦”的歌曲里,“22岁的朱践耳依然没有血脉贲张,而只有热切的期盼。”
部队文工团里,条件虽艰,朱践耳却心情愉悦,老毛病只犯过一次就奇迹般地未再复发,令他感慨“是革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!”1947年初,为山东莱芜战役而作的《打得好》成为他的第一首代表作,收入《淮海战役组歌》,代表了当时解放军音乐最高水平。
“《打得好》我从小就听过,那时朱践耳先生的创作天才就展现出来了。”陈燮阳回想与其二十多年合作,“朱先生的人品、艺品几乎是完人。温文尔雅的长者,说话时轻声轻气,但是他的内心非常强大,出来的音乐,跟他的表面性格完全不一样。”
作曲家何仿1948年第一次见到朱践耳便说,唱了这首歌,“以为你一定是个高大的北方汉子,原来是个文弱书生!”几十年后,朱践耳回想此事,似有所感,“自己在生活性格和艺术性格方面确实存在着明显的两重性。”
“西麟,要绵里藏针啊。”对王西麟这位口无遮拦的后辈,朱践耳曾多次这样劝勉。“表面上说话四平八稳,心里和音乐里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。”王西麟说。朱老身后,他撰文重提“三级跳”:从简谱到交响乐思维跳跃,改革开放后又向现代音乐先锋乐派大踏步地迈进,“根据地出来的简谱派作曲家中,完成这艺术超越三级跳的,可以说仅朱先生一人,何其难能可贵!”他多次向本刊记者感慨,世人对朱先生的认识和尊重还远远不够。
英雄的诗篇
2015年9月28日,正值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,朱践耳根据毛泽东诗词创作的“交响曲——大合唱《英雄的诗篇》”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上演,距离该作上海首演已有53年。现场指挥陈燮阳说,一个月前上交演出全剧并录音制作了唱片,“了却了朱老最大的心愿。”
当时,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黄晓和与朱践耳共同在现场看谱、听排练。他还记得,自己听得热泪盈眶,情不自禁地说:“朱哥哥,你的音乐太感人了!你生前获得这样的成就,应该知足了!”没想到朱践耳竟两手蒙住脸哭出了声……
1954年,朱践耳被选派赴苏联留学,《英雄的诗篇》就是他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的结业作品,也是他“交响梦”的正式起步。当时,他深感自己水平有限,乐思枯竭,主动要求从三年制研究生降格为五年制本科生。
继习作《节日序曲》后,《英雄的诗篇》是朱践耳第二首被苏联电台永久收藏的曲目。其主科老师巴拉萨年评价,作品非常大胆,创造了对中国而言还没有过的非同一般的宏伟形式,“丰富的和声综合体,有意思的复调手法。如果还有补充的话,那就是您出色的管弦乐嗅觉,这种效果应该无疑是来自个性。”
然而,正准备排练录音之际,1960年夏,中苏关系破裂,合作中止,该作未能在苏联上演。朱践耳毕业回沪,1962年《英雄的诗篇》过审演出,两年后被要求修正新版本后重演。
朱践耳留学期间受诬告背了处分,工作调动也不顺,来到了上海歌剧院而非上海交响乐团,想到交响乐在当时文化意识之中毫无地位和价值,他心灰意冷。而《英雄的诗篇》总谱被出版社退稿的遭遇,也让他意识到,自己在苏联留学时所作的有关中国交响乐的追求和实践,遭到最终宣判:“此路不通!”
后来他眼见各省管弦乐队被解散,小提琴演奏员受命改拉二胡,吹长笛小号的改吹竹笛和唢呐,甚至有钢琴家的手指被打断,“交响梦”彻底粉碎了,一搁就是18年。
他被借来调去,参与集体创作,没吃什么苦头,却耽误了子女前途。一贯直言的夫人舒群也接连被整。身处上海舞蹈学校《白毛女》剧组,她先后被扣上“走资派、炮打样板戏、炮打江青”的三顶大帽,被红卫兵接连批斗毒打十天,被关牛棚一年三个月,患过血尿、差点跳楼。
对自己“文革”前和“文革”中的作品,朱践耳的感受截然不同,前者在努力说真心话、实在话,比如创作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是读了《雷锋日记》,看到一个“崭新的人、纯粹的人、心地透亮的人”那活生生的形象;而后者则完全是“领导叫干什么,我就干什么……究竟写了些什么音乐,我已毫无印象。”
1993年,朱践耳精简和修改《英雄的诗篇》,并加写了一首男低音独唱《娄山关》,其基调悲壮,“残阳如血”一句隐喻着斗争的艰险,“付出的血的代价极大。”他把评价长征的任务交给历史学家,自己歌颂“为人类的美好理想而甘愿吃苦献身”的“可敬可爱的人民英雄”。“没有英雄的民族,是悲哀的民族,一个仅仅以英雄为旗帜的民族,也是悲哀的民族。”在《创作回忆录》里谈到这部作品的尾声,朱践耳引用了这段话。
生活启示录
六年迷途,十年荒唐压抑,两年反思。1960到1978,18年断层,令朱践耳感到不仅毁了“交响梦”,也使“革命梦”大大被扭曲和变质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他“像火山爆发一样,乐思如泉涌”。
完成于1986年的《第一交响曲》酝酿了十年,虽以“文革”为题材,却意在谱写一部人类的“命运交响曲”。早在1976年,创作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弦乐作品《怀念》时,朱践耳走访了一批群众,他放弃了“一个廉价的大团圆、大辉煌的结局”,借鉴贝多芬《第五交响曲》的写法——“孤岛”时期的青年朱践耳,就曾注意过其展开部末尾突然出现的一个插部——那是轻声出现的“命运主题”,如哀鸣,如回顾,如警示。
此前为纪念张志新烈士所作的《交响幻想曲》里,愤怒的声声大鼓后,一声恐怖的嘶响,暗示着主人公被割喉的惨剧。她的遗作《谁之罪》里的四音,在尾声部分隐约可闻,余音绕梁。
彼时,朱践耳听懂了肖斯塔科维奇的《第十交响曲》、《第十一交响曲》;在1984年的莫斯科第二届国际音乐节上,苏联人也听懂了他的《交响幻想曲》。时隔24年重访莫斯科,朱践耳更大的感慨在于自身作曲技法的落伍,下决心作根本的创作转型。
于是他在花甲之年坐进上海音乐学院的课堂,与学生们一起听桑桐关于多调性的系统分析、听杨立青对梅西安作曲技法的分析、听陈志铭关于十二音无调性体系的系列讲座等等,一时传为佳话。
他在《第一交响曲》里,以十二音列为“骨架”,加上18个重复音(“肉”),分别创作两个主题,传统调性旋律转变为无调性不协和音,一如人的异化;一夜梦中惊醒,大呼“悲剧没写够”的他,紧接着创作续作《第二交响曲》,全曲只用源于人声呜咽音调的三个音,组成对称配套的十二音列,加之特殊的乐器锯琴,将一股“从现代迷信中彻悟过来的痛楚、内疚、悔恨和愤怒”的音流猛扣心弦,“悲时,揪心泣血;愤时,撕心裂肺。”此时朱践耳眼里的十二音序列技法,就像七巧板般变化多端、趣味无穷。
贵州、云南、广西、西藏等地都是他的课堂。上世纪80年代初,带着一架简陋的录音机,六十多岁的朱践耳骑马过峻岭,深入偏僻村落,一走八九个月。某年春节在苗岭,为了与老乡“成为一家人”,他吃下生牛苦胆,一时上吐下泻,差点酿成“险情”。
但是每当和人回忆起那些令他终生难忘的民族音乐,眉发雪白的朱践耳都会缓缓闭上眼睛,如同仙游:贵州黎平的某个下午,刚听完犹如西方现代派音乐音响的芦笙队比赛,半夜又听一阵不同的音乐,循声而去,只见几个青年男女正围着篝火唱着侗族情歌;云南丽江,纳西族的一首爱情对唱歌,毫无曲调可言,背后却是一个争取婚姻自由的“殉情”故事……
朱践耳深为感动,“他们的爱情对唱,并不需要什么华丽旋律的装饰,要的只是真诚心灵的自然吐露。”他把这些创作感悟写在一篇《生活启示录》里。曾经觉得西方十二音与中国音格格不入的他,庆幸终于在中国民间音乐中找到了“根”,现代化与民族化结合的音乐之窗由此打开。10月21日,上海交响乐团上演朱践耳“天地人和”作品音乐会,其中曲目堪称典范:
《黔岭素描》里“吹直萧的老人”,《纳西一奇》里的“母女夜话”,都直接来源于对少数民族原生态材料的采风;《第三交响曲“西藏”》的第一乐章,描写世界屋脊上的展佛、跳神和藏戏,表现藏族同胞性格中的两个侧面:神秘与明朗;而开篇曲《唢呐协奏曲“天乐”》,则神奇地实现了唢呐这件极富个性的中国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的“油水相融”。
有人说,“朱践耳的交响乐作品,上关乎天地,下注重人性、人格和人的命运,所以他的交响音乐会称作《天地人和》,很符合他的意境和追求。”
入世“江雪”
为朱践耳赢得第十五届“玛丽·何赛皇后”国际作曲比赛唯一大奖的《第四交响曲》,构思于1989年,以竹笛为独奏乐器,历史兴亡的悲叹升华为老庄哲学的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以及万物皆“从无到有,从有到无”。
1991年“上海之春”首演后的研讨会上,有权威人士托人带来口头意见:“毫无民族性可言,丢掉了竹笛的本体美,专吹些怪腔怪调的、不入耳的东西……”
与其他许多作品一样,来自业余爱乐者的支持,反而给了朱践耳极大鼓舞:
“不追求传统旋律,而着重表现一种幽深高远的意境。俞逊发的笛子很绝,把人的心都勾出了”;“艺术家应该有超前意识,要有‘听不懂’的、使人产生联想、有拒绝的东西,《第四交响曲》就是这样的”……
在这个过程中,朱践耳与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结下深厚情谊。2015年9月,协会成立三十周年,93岁的朱践耳在夫人和上交团长周平的搀扶下坚持出席,与大家签名留念。
不过,朱践耳坚持在《创作回忆录》中将“好的、不好的”评论都记上。这也是受贝多芬交响曲总谱全集的影响。他曾给王西麟去信,诚意提醒他,在音乐会节目单上罗列太多好评不妥,“在对待音乐评论时,要除去一个最高分,但得保留一个最低分,才是更明智的。因为‘最高分’使自己头脑发热、自我膨胀,而最低分却是清醒剂。”
他也曾好奇地问爱乐者,为何某些音乐专家难以接受的作品,你们却能接受呢?答曰:“他们有老框框,我们没有。我们接触不少现代艺术,如文学、美术、电影,和音乐都是相通的。”
《朱践耳交响曲集》代自序中写道:“举凡中国的民间音乐、文人音乐、戏曲音乐、宗教音乐等等皆可兼容并蓄;书法、国画、诗词、戏剧等等皆可触类旁通。尽可能地增厚作品的文化涵量。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,不论古今中外,都可拿来,为我所用。”
第十交响曲《江雪》以柳宗元的名诗为题材,京剧名家尚长荣录制了三段吟唱录音,配以古琴大师龚一的琴音,加上从《梅花三弄》里“提炼”出来的十二音序列,意境独特。杨立青在研讨会上讲出的两点联想都“中了”:嵇康和狂草。
然而,在朱践耳身后,围绕这部作品,对其人生境界产生了截然相反的解读。出世还是入世?夫人舒群和好友黄晓和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。黄晓和称,柳宗元因参与革新而遭保守势力镇压,其在严峻和恶劣的大环境中展现“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独立人格精神,其实非凡,有横扫千斤之力度”,这部作品非但没有丝毫消极情绪,而且充满正气、锐气、浩气。
直到今天,舒群仍对“钟鼓奖事件”未有处理结果耿耿于怀。2007年10月30日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国际作曲比赛,唯一大奖涉嫌“抄袭”时任作曲系主任何训田之作,获奖者被指为其“情人”。此后,何训田公然拳打表示异议的该系教师朱世瑞,引发轩然大波。朱践耳挺身而出,要求院方对事件作出处理,并在期刊上发表《“钟鼓奖”事件亲历记——向音乐界的汇报》,由此卷入两场官司,消耗了许多精力。
睡吧,孩子
“至诚至真,乐之灵魂。至精至美,乐之形神。若得万一,三生存幸。孰是孰非,悉听后人。”这是朱践耳的座右铭。
相识二十多年,陈燮阳想不起来,朱践耳还有哪些爱好,音乐是他的全部,似乎也是唯一的乐趣。他过去位于武康路的家很小,为了不影响妻儿休息,硬是在逼仄的厕所间里搭出一个“工作室”;后来孩子大了,“工作室”搬到了湖南路,别人下班,他上班,笔耕不辍,常常一写就到深夜。1994年,朱践耳去美国探亲十个月后,竟带回四部新写的交响曲,原来他什么景点都没去。
陈燮阳还记得,今年6月在北京国交指挥复排《英雄的诗篇》时,朱践耳托女儿带来一封信和巧克力,皱巴巴的纸上写着端正的字:“陈燮阳老友,排练太辛苦了,吃点巧克力。”
以往的排练,他总会坐在指挥旁边,在一张纸上标明每个细节应如何处理。他的手稿出了名的端正精准。夫人舒群常劝他,“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写谱子。”但每次都被他反驳,“先生教的:每个符头、每根线都要对齐,连在哪里翻谱都要算好,方便指挥、演奏员阅读。”
作曲的人常把屋子搞得乱七八糟,但朱家永远干干净净。他总穿工作服创作,胳膊上套着袖套,像进工厂的工人,一大把铅笔削得非常细,笔头一秃就放在边上。
90年代初,朱践耳做过一次较大的肠胃部手术。作曲家秦文琛当时还只是一个学生,买了两包饼干去医院看望,才走到门口,被师母舒群拦下来,直接批评他,“你年纪轻轻就搞这种东西。”朱践耳躺在床上,话都说不利索:“拿…拿…拿作业了吗?”秦文琛回去拿来作业,朱践耳才允许学生进门,然后自己从病床上直起身来上课——他第二天还要动手术。
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陆培说,30岁时与朱老谈话,“才说了几句,他掏出本子来写,让我非常非常惊讶:一个大作曲家,不仅在听我说话,还把它记下来。”
“他永远都笑呵呵,一听说什么新奇的东西,就瞪着惊奇的大眼睛:‘啊,真哒?’”朱践耳的学生、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孔聪回忆,“好的教育是什么呢?不是把你灌满,而是把你点燃。那些年我们上课就像玩一样,从作品里去找好玩的东西,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,他乐我也乐。”
因为写作《江雪》的毕业论文,十几年前,本科生桂俊杰与朱践耳成了忘年交。最后留在他记忆中的朱践耳,有些老糊涂,一句话会重复八遍;在家旁的元龙音乐书店偶遇,只有一个眼镜腿挂在耳朵上。他写过的自勉“歪诗”俨然成真:“老而犹顽,顽似一童。童心率真,真无忌惮。”
2012年,这位青年指挥家率上海少儿广播合唱团赴维也纳美泉宫,首演了朱践耳的童声合唱与双钢琴作品《月亮弯弯》。在遗体告别式上,桂俊杰特别遗憾,“没能以《月亮弯弯》送先生最后一程。”
这首歌改编自《第九交响曲》第三乐章结束段的童声合唱《摇篮曲》。从第六到第八交响曲,包括写给香港回归、叙述我国历史的《百年沧桑》,朱践耳都没有简单给出光明圆满的结尾。他所作的这最后一部交响曲、也是“迎新世纪”之作,同样带着悲悯,却又暗藏希望。
10月21日的“天地人和”音乐会以此收官。爆炸的鼓声、惨叫的木管组戛然而止,一声丧钟似的铜磬引出大提琴独奏的吁叹,随后是童声合唱:
月亮弯弯,好像你的摇篮;星星满天,守在你的身边。绿色的小树陪你一同成长;爱心的甘露滋润你的心房。虽然乌云会把月光遮挡,虽然暴雨会也会无情来摧打,过了黑夜,迎来灿烂朝霞。
早在1940年,朱践耳也创作过一首《摇篮曲》:“睡吧,睡吧,孩子啊,过了黑夜就天明……”音乐会次日的研讨会上,许多音乐界专家谈起被刺耳之后的纯净童声感动。“他的一生不忘初心。”作曲家奚其明说,“在他眼前没有丑和美,只有真。只有真了,丑和美就在一块,不协和音就协和了。”